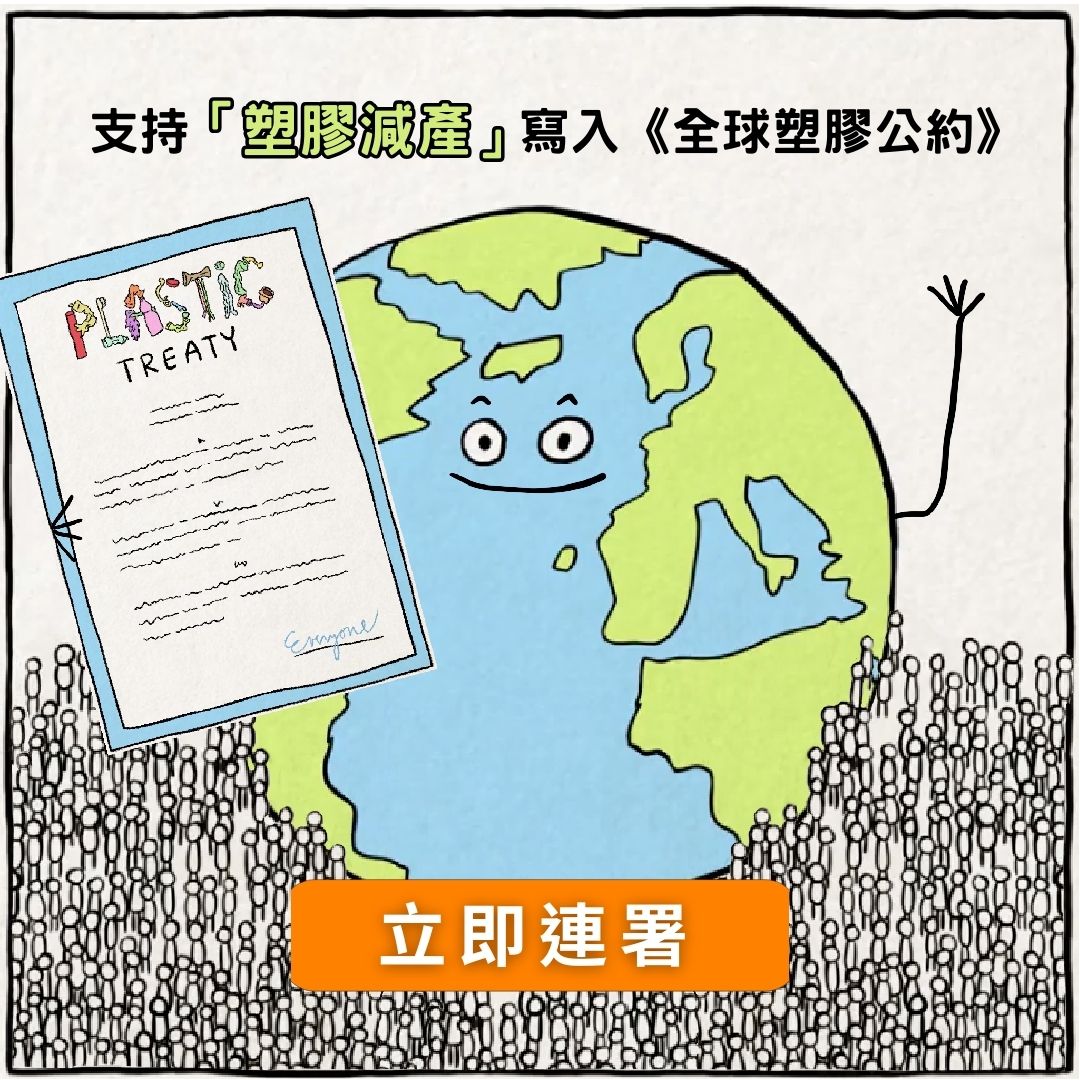淨灘、回收能根絕垃圾問題?解決塑膠污染的四大錯誤解方
塑膠生產爆炸性增長,您我的身體和生態系統的各個角落都逃不過塑膠污染。然而,化石能源公司、石化產業以及眾多知名品牌等主要污染元凶,仍然採取錯誤和虛假的手段謀取利益,例如回收、淨灘以及製造生物可分解塑膠。為什麼這些方法無法真正解決日益嚴重的全球塑膠污染危機?
文章目錄
解決塑膠污染的四大誤區
回收——逾 9 成被當垃圾
長久以來,回收被吹捧為減塑解方,尤其可口可樂、百事、雀巢、聯合利華等大企業大力宣傳塑膠回收再利用能解決污染問題。
但是,現實並非如此樂觀。
全球僅有 9% 的塑膠廢棄物回收再利用,其餘則被焚燒、掩埋或最終流入環境,例如海洋一年就吞下 1,270 萬噸塑膠。即使在發展塑膠回收相對領先的國家,其家庭塑膠回收率也往往遠低於 50%,其中再製成其他用品的比例更是微乎其微。此外,再生塑膠品質常常無法令人滿意,製造商自然不願採用。
因此,過度依賴回收,無異是延續了「取得—製造—丟棄」的線性消費模式,且使用壽命非常短,根本無法根絕塑膠生產過剩和過度消費的問題。(延伸閱讀:每年1270萬噸塑膠流入海洋!失控的塑膠污染成為全球環境問題)


另外,化學回收(Chemical recycling)——將塑膠分解為分子物質(molecular components)再製成新產品——被業界代表人士(如歐洲塑膠生產商遊說團體 PlasticsEurope)盛讚是「革命性解決方案」。
然而,化學回收的過程不僅消耗大量能源、操作複雜,更牽涉多道化學反應、產生排放物,說是回收再利用,卻是以另一種形式污染環境。未來能否大規模推行還有待觀察。
以上兩種回收方式(物理與化學回收)之所以備受質疑,主要原因在於塑膠難以徹底回收分類和充分清潔,而且再加工過程會產生毒物、對環境並不友善,多數塑膠原本就是用有毒物質製成或遭有毒物質污染,若回收再利用並不符合經濟成本。(延伸閱讀:《永恆之毒》報告:塑膠回收後更毒,衝擊人體、環境、食物鏈)
淨灘——源頭不減,永遠撿不完

Boyan Slat 創立的非營利組織荷蘭「海洋清理行動基金會」(The Ocean Cleanup)開發創新的海上垃圾攔截機(Interceptor),透過洋流和風向等自然力量被動捕獲和集中塑膠碎片;與此同時,綠色和平也在世界各地投入淨灘和清理行動。
然而,這些行動就好比水龍頭還在流動時拖地板:短暫解決了塑膠污染的症狀,但幾乎無法防止塑膠持續流入生態系統。如果上游沒有減少塑膠生產,那麼淨灘、淨河、淨山將永無止境地循環下去,也無法跟上塑膠污染進入環境的驚人規模和速度。
如果為了查明塑膠污染來源、辨識哪些企業是最大的污染源頭,淨灘是非常有力的行動,不僅能倡議企業為其產品包裝所產生的塑膠廢棄物負起責任,更可推動源頭減量、重複使用、重複填裝等系統性改革。此外,淨灘也具教育意義,綠色和平完成淨灘活動後提醒公眾,如果源頭沒有減量,垃圾不會因淨灘變少。(延伸閱讀:這些品牌竟是全球塑膠污染榜首,你能怎麼做)
生物可分解塑膠——無特定處理條件就無解
生物塑膠(Bioplastic)是指部分或全部原料取自可再生生物質(如植物)或是生物可分解的塑膠材料,亦或是兼具兩種特性。許多食品及消費品業者選擇用生物塑膠作包裝材質,藉此宣稱「環保和減塑」,以逃避企業責任。但生物塑膠真的比較環保嗎?
這類塑膠材料雖然可隨時間分解成較小的碎片,但通常需要特定的條件,像是高溫、高濕的工業堆肥環境,而這些條件在大多數環境中都無法滿足。研究人員也發現,許多被稱為生物可分解的塑膠最終仍流落海洋或垃圾掩埋場,持續數年沒有明顯分解,反而產生大量的微塑膠。(延伸閱讀:生物可分解塑膠比較環保?真正的塑膠污染問題解法其實是...)

如果將生物塑膠作為的石化塑膠的替代品,只會分散您我的注意力,拖延真正解決問題的根本之道。畢竟,這樣的做法無非是從另一個源頭生產塑膠,沒有真正減少塑膠使用。
吃塑膠的細菌——難以預料的減塑偏方

日本京都工藝纖維大學(Kyot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教授小田耕平(Kohei Oda)在 2001 年發現吃塑膠的細菌,這項驚人發現在網路社群引起熱議,也喚醒人類以自然解決塑膠污染的期盼。
的確,在嚴格受控的實驗室環境中,吃塑膠的細菌展現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塑膠分解能力,但要將這一過程大規模應用於工業層面並不容易,而且將經過基因改造的細菌釋放到生態系統中,可能破壞脆弱的生態平衡或產生難以預料的後果。
《全球塑膠公約》是解決塑膠污染的關鍵!
相信關心環境的您已經發現,回收、淨灘、生物可分解塑膠以及吃塑膠的細菌四個減塑誤區,都是從末端解決塑膠污染危機,忽視了問題的核心癥結——塑膠產量失控成長。全球最需要的解方,應該是從源頭關緊水龍頭,減少塑膠產量。(延伸閱讀:減塑的關鍵方案:採用「重複使用」模式,推動《全球塑膠公約》)
聯合國《全球塑膠公約》是一份解決世界各地塑膠污染問題的國際協議,其規範涵蓋塑膠生產、消費到棄置整個週期,制定規範標準與實行目標,是全球源頭減塑的關鍵工具,被喻為自《巴黎氣候協定》以來最重要的國際環境協議。
衝刺吧!談判《全球塑膠公約》的全球領袖!

目前,來自世界各地的政府、企業和環保團體正在積極談判《全球塑膠公約》的條文內容,目標在 2024 年底達成一個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正式協議,意味著簽署的國家必須嚴格遵守協議內容。今年 11 月 25 日至 12 月 1 日,多國領袖將齊聚韓國釜山,展開《全球塑膠公約》第五次談判會議(INC 5),這是預期的五輪談判中最關鍵的一役。
因此,我們必須緊抓這次第五輪談判的關鍵機會,綠色和平代表團將全力推動聯合國代表達成以下目標,爭取一份強而有力的《全球塑膠公約》:
- 2040 年將塑膠減產 75%,有助全球將升溫控制在攝氏 1.5 度內
- 推動低碳、零廢棄和重複使用的規範
- 制定具法律約束力的條文,涵蓋從生產、消費到棄置的整個週期,並落實污染者付費原則
- 以人權為核心,消除環境不公與社會不公
目前全球已有百萬人連署響應《全球塑膠公約》,這數百萬雙的公眾之眼不僅壯大了全球減塑運動的聲勢,也讓綠色和平代表團能將您對終結塑膠污染的期望清楚呈現於聯合國談判桌。透過這股強大的關注壓力,我們正促使政治領袖與企業代表將「減少塑膠產量 75%」和「推廣重複使用」納入公約的共同目標!
您的連署都不僅僅是一個名字,更是創造關鍵改變的力量。綠色和平代表團正將您的目光帶到決策核心,為地球和未來世代發聲。您的參與至關重要,現在就加入連署▼